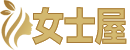昆曲《牡丹亭》 600年昆曲藝術當代煥新,大劇院版重逢《牡丹亭》真的很美
然而,作為一部昆劇作品,有美,有劇場觀,有當代感,是完全不夠的。表演藝術,才是真正支撐起這門傳統藝術的全部基石。
尤其是對于《牡丹亭》這樣的劇種代名詞而言,幾百年來有太多的版本,幾乎所有的昆曲演員都演過這個戲,對于昆曲閨門旦和小生演員來說,這更是檢驗他們昆曲表演水平乃至決定江湖地位的試金石。
因此,在各種版本的《牡丹亭》里,歷代昆曲演員都致力于把表演藝術能夠打磨到更好,但有時,這種循環復刻的藝術傳承,也會因為太過熟稔,而變得缺少新的意趣。而在當下,更普遍的情況是,對于《牡丹亭》這樣的傳統劇目演出,因為太重視藝術技藝,“人物塑造”這樣的戲劇命題,往往會被輕視甚至忽略。
在這一版《牡丹亭》里,杜麗娘和柳夢梅不再只是閨門旦和小生的某種形象代言,他們在昆曲的表演行當之外,有了更完整的人物性格和變化。不是說別的版本沒有,但在這個版本里,因為劇本和導演的新構思昆曲《牡丹亭》,因為演員一人演完全場,并在傳統戲之外有了一些新的變化和創作,這種一以貫之的人物塑造和層次豐富的表達,便顯得更為突出。
也因此,這是一個可以稱為“作品”的《牡丹亭》,而不是一次簡單的新版《牡丹亭》演出。
導演馬俊豐是個80后,他導演過很多作品,其中更多是受到年輕觀眾喜歡的話劇。對于一個戲劇作品的整體質感和人物把握,以及如何建立和觀眾的情感交流昆曲《牡丹亭》,也許是他更為關心的命題。據說,在排練場上,他不斷啟發演員,要思考柳夢梅和杜麗娘在彼時彼刻的情感關系和狀態。這在某種程度上,正是放大了昆曲表演極端細膩的優長。

但作品觀念最后的完成,必須依賴于演員。對于昆曲而言,要實現傳統和當代兼顧的舞臺面貌,表演者必須要有極為扎實的傳統功底,以及極其跟得上時代的舞臺觀念。缺一不可。
幸運的是,張軍和單雯,都是這樣的演員。
兩人都是當下昆曲界的領軍人物,演了太多太多的《牡丹亭》,于他們而言,這個戲和這兩個角色,實在是太熟悉,可以說伴隨著整個藝術生命。在昆劇唱做表演的傳統功底上,他們都可以說是這一代演員的最好水平。
但這一次,這兩個已經在藝術上相當成熟的昆劇中生代藝術家,竟是第一次在舞臺上合作。不得不說,這是一次美好“重逢”。“是那處曾相見?相看儼然,早難道好處相逢無一言。”杜麗娘和柳夢梅的對手戲,太需要棋逢對手,才能碰撞出光彩。而張軍和單雯,正是實力相當的一對CP。他們在舞臺上被互相激發,展現出自己最好的舞臺狀態,煥發出新的表演質感。

單雯一直都是美的。憑借《牡丹亭》摘得中國戲曲最高榮譽梅花獎榜首,她師承自張繼青的杜麗娘一直是被認為美到極致。但在這一版中,她讓杜麗娘在“美”之外多了一份“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精神力量。并且在不同的場次中,這種精神情感有了更豐富的層次。這是演杜麗娘最難把握和呈現的,需要演員發自個人的內心力量,以及一種對表演的真正領悟。

而張軍對柳夢梅更可以說爛熟于胸,演出版本歷經無數,可能還是迄今唯一一個曾經演過全本55出《牡丹亭》的小生演員。但這么多年,觀眾其實鮮有機會看到他演出這么多戲份折子的《牡丹亭》,戲長三個小時幾乎沒怎么下場。因為這個版本的“完整性”,人們看到了一個少年的、含蓄的、深情的柳夢梅。而不僅僅是常演“驚夢”里那個紙片一般單薄的古代書生。在《冥誓》這樣的段落,柳夢梅的至情力量比杜麗娘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張軍這么多年的舞臺角色積累,也是他作為一個觀念開放演員所具有的人物塑造能力。
當然,還有一點比較關鍵,在舞臺上,這真的是一對才子佳人,很美,很對。賞心悅目,看戲曲很重要的一件事,是不是。
最后還是想說,《牡丹亭》的家底實在太豐厚了。這一版《重逢牡丹亭》,雖然跳脫了傳統演出版本的束縛,但卻尊重著傳統表演的規范,一詞一曲、一招一式皆有出處,每一分鐘的表演,都顯得美不勝收。沒有扔掉600年的家底,而是用當代劇場藝術對傳統藝術進行放大、聚焦昆曲《牡丹亭》,照亮。如同把一個古董文物放進博物館最好看的展廳,用最當代的觀念布展,用最高級的燈光映照,對懂和不懂的觀眾,都是吸引。
《重逢牡丹亭》是一次古典和當代的雙向奔赴,也是一個傳統藝術如何煥新的思考范本。
免責聲明:本文系轉載,版權歸原作者所有;旨在傳遞信息,不代表本站的觀點和立場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需轉載,請聯系原作者。如果來源標注有誤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權益或者其他問題不想在本站發布,來信即刪。
聲明:本站所有文章資源內容,如無特殊說明或標注,均為采集網絡資源。如若本站內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權益,可聯系本站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