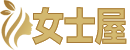談談越劇的傳承
談談越劇的傳承
在2007年和2008年之交,有兩條越劇方面的信息大家想必都聽到過了:一是越劇經典《紅樓夢》拍成了兩個版本的電影:鄭國鳳、王志萍主演的徐、王版和趙志剛、方亞芬主演的尹、袁版。電影在上海公映后,觀眾爭相觀看,上座率奇高;二是上海越劇院復排了經典名劇《西廂記》,由方亞芬、錢惠麗、張詠梅、吳群主演,并作為春節賀歲劇公演。消息傳出,許多網友歡呼“多年的愿望終于實現了”,看過彩排的更是在網絡的越劇論壇上贊不絕口。這些耳熟能詳的經典為什么受到歡迎,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大家看到傳承正越來越受到重視,老藝術家創造的藝術精品,被后輩很好地傳承下來,煥發出活力和新的光彩。
其實,越劇從誕生至今100多年來,能夠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不斷發展,取得輝煌的業績,是一代又一代從業者認真傳承的結果。有傳承,劇種的生命才得以延續,年輕的新人才得以脫穎而出,前輩創造的成果才得以保存、積累,劇種的文化品位才得以提高,觀眾的欣賞要求才得以滿足。現在,越劇已被選定為受國家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這促使我們進一步深刻認識傳承的價值、意義和重要性。
傳承,主要指后輩向前輩學習,把前輩的藝術成果學下來,轉化為自己的東西。它與戲曲教育的含義有重疊,但又不完全相等,因為有些內容不是通常說的“教育”所能涵蓋的。傳承總包括兩方面:傳承者和被傳承者,通俗的說法就是師傅和徒弟,或者老師和學生。越劇的傳承,解放前主要靠科班,解放后主要是靠戲校。
科班是一種小型的民間教育機構,一般有一個主教師傅和兩三個輔助的教師,學徒一二十人或二三十人。越劇有科班,是從1923年辦起第一個女班開始的。這個女班由嵊縣商人王金水出資,聘請戲路較寬的男班藝人金榮水為師,生旦凈丑都由他傳教;后來,又請王和千、任阿求教武功。第一個女班誕生后,一方面由于社會偏見受到歧視,另一方面由于演員年齡幼小演技稚嫩,生存艱難,此后六年沒有新的科班。直到1929年,才辦起第二個女班。從1930年起,嵊縣的女子越劇科班如雨后春筍,兩三年間就興辦起幾十付科班。這些科班主要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子弟班”。藝徒都由家長自負膳宿,師傅的膳食、工資和其他開銷由藝徒平均負擔,沒有老板和經紀人,演出收入除膳食開支外,按月分攤工資。如1929年開辦的新新鳳舞臺,就是典型的子弟班。
第二種是“拼股東科班”。辦科班經費由數位股東以入股的形式拼湊,以后演出收入也按股份提成。如1930年開辦的、曾培養了姚水娟、竺素娥的群英舞臺,1931年開辦的、曾培養了王杏花、邢竹琴的越新舞臺,1933年開辦的、曾培養了袁雪芬、傅全香的“四季春班”,都屬于“拼股東科班”。
第三種是老板獨資開辦的科班。這類科班更多。如1930年開辦的、曾培養了筱丹桂、商芳臣、周寶奎的高升舞臺,由長樂大昆村邢惠彬出資,崇仁鎮裘光賢任班長,掌管班內一切事務;1931年開辦的、曾培養了尹桂芳、毛佩卿的大華舞臺,由坎頭村王水老出資并當班長。這類科班,當然以盈利為目的。
除了嵊縣之外,在浙江的紹興、寧波、新登、臨安、諸暨、余姚、金華、三門等地也陸續辦起女子科班;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女子越劇在上海站住腳跟后,在上海也辦了十副以上的科班,如“四季班”、“陶葉劇團”、“忠孝班”、“玉字班”等等,培養出戚雅仙、畢春芳、陸錦花、呂瑞英、陳少春、茅勝奎等一批著名演員。
這些科班一般都是由男班藝人執教,有些也請京劇、紹劇藝人教武戲;規定的學習時間三到四年不等,多數學半年甚至三個月就“串紅臺”,即實習演出,以后在演出過程中邊演邊學。多數科班要求學員從一開始就寫“關書”,這種“關書”是一種契約,學員保證學戲期間生死病傷,各憑天命,滿師以后再幫師若干時間。科班帶有封建性質,但在解放前是一種普遍存在的形式,對于越劇傳承、人才培養起了重要作用。
建國后越劇人才的培養,主要依靠國家舉辦藝術學校,同時開辦各種培訓班與招徒隨團培養。
1954年,華東戲曲研究院開設了越劇演員訓練班,后轉為上海市戲曲學校的越劇班。1958年浙江建立浙江文藝學校(后改浙江藝術學校),另有南京市戲曲學校(后為江蘇省戲曲學校),都設有越劇班。由國家舉辦的越劇藝術人才培訓班,完全按照國家制訂的中等藝術專科學校的規范教學。1960年,上海越劇院及部分區縣劇團辦起了學館和訓練班。靜安區、南市區、南匯縣的戲曲學校和虹口區專業劇團學館均開設越劇班。浙江、江蘇一些縣市也成立一些戲校或學館。這些學校、學館除傳授專業技能外,還開設文化課,提高學館綜合素質。
除科班和戲校外,還有兩種形式:一是個別拜師學藝。越劇早期,男班藝人都從唱書轉來,沒有戲曲表演基本功訓練,也沒有科班,后繼者一般都是個別拜師學藝,技藝由師傅口傳心授。越劇博物館有一張男班藝人師承譜系表,列出南派、北派早期四代藝人的傳承關系,很清楚。到女班時期,少數人仍采取個別拜師學藝方式,如丁賽君和姚月紅,就是由魏銀鳳、姚水娟收為徒弟帶教成才的。二是隨團培訓。1946年,雪聲越劇團首開劇團招收學員隨團培訓的先例,隨后東山、玉蘭、少壯等劇團也加仿效。如金采風、馮文錦等是雪聲劇團的隨團學員;朱東韻、陳東文等是東山越藝社的隨團學員;方資潔、江敏莉等是玉蘭劇團的隨團學員;陸依萍、沈鳳英等是少壯劇團的隨團學員。隨團學員跟隨劇團演出,在實踐中學習,并就近得到名家的指點。
應該強調指出:科班也好,學校、學館也好,都是重在打下基礎,學員在傳承方面只是邁出了第一步。第一步當然是重要的。因此,教師的水平、教戲的方式、課程的安排,直接關系著教學質量。名師出高徒雖不能絕對化,但不是沒有道理。如果老師不能把一流的藝術教給學生,學生也就不可能傳承到越劇的精髓。但是,正如俗話說的:“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打下基礎、邁出第一步之后的路還很長、很長。尤其是越劇,與京劇、昆劇相比,科班學戲帶有速成性質,往往半年甚至三個月就“串紅臺”,學到的東西有限;戲校、學館的學制也少于京昆。一個優秀的演員,在出科或畢業后,總是孜孜不倦地向前輩學習,千方百計把前輩的藝術精華、真本領學到手。解放前在戲班,流行的是“偷戲”,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徐玉蘭等老藝術家都在回憶錄中談到過“偷戲”的經歷。譬如袁雪芬出科后,在浙江蕭山與名旦王杏花同臺演出,她就在臺上注意記下王杏花的唱腔和身段,下了舞臺,偷偷躲在“出將”、“入相”門簾后或舞臺旁屏風后,用心地學。這樣,接下來到杭州演出時,她就被觀眾稱之為“小王杏花”。解放后,老師教學生都非常無私了,但不是從戲校畢業后就一勞永逸了。傳承仍是個持續不斷的過程。譬如方亞芬,從浙江調到上海后,先進上海戲校學習,畢業后,她師承袁派,既受到袁雪芬的親自教誨、悉心指點,同時她又刻苦鉆研,深入體會,不斷在實踐中提高,因此成為公認的優秀袁派傳人。趙志剛在上海越劇院學館最初學老生徐天紅派,1978年因為偶然的機緣改學小生,學的是范派、徐派、陸派,1979年尹桂芳越劇流派演唱會使他對尹派著迷,不久他成為尹派私淑弟子,后登堂入室,成為尹桂芳嫡傳弟子,得到恩師的親自指教。趙志剛傳承尹派也是堅持不懈,他通過復排《何文秀》、《浪蕩子》、《紅樓夢》等尹派名劇,在傳承尹派方面成績突出,受到觀眾熱烈歡迎。
越劇傳承方面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特點:
一、越劇的傳承,是“活體傳承”。
越劇已經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依據《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被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工具、實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這一定義揭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內涵,在于它是一種精神的實踐、經驗的積累、技巧的形成和藝術的展現。越劇和其他戲曲一樣,其精神的實踐、經驗的積累、技巧的形成和藝術的展現,統統存在于活著的人身上。遺產的傳承者是活著的人,被傳承者也是活著的人,都有思想,有感情,有各自的生命體驗,因此稱“活體傳承”。這就與通過機械、電子等手段大批量復制完全不同,與僅僅靠著讀曲譜、聽錄音、看錄像刻板學習也不同。“活體傳承”有幾個特點:一是傳承者在每個時期的唱腔、表演可能有很大不同,甚至可以說,沒有兩場戲百分之百、一毫不差完全相同。最近有同志整理了袁雪芬在解放前灌制的全部老唱片,聽一遍就會發現,同一個劇目的唱法在不同時期是不一樣的。聽聽傅全香的《梁祝》、《情探》也會發現不同時期各有不同。其實每個藝術家都是這樣,每場演出總有活動或小的變異。被傳承者在學習時就應該有全面清楚的認識,不能瞎子摸象,坐井觀天,把某個版本、某次演出奉為絕對的樣板。二是既然技巧、藝術成果都在人身上,那就是人在藝在,人亡藝亡,如果不抓緊傳承,就完全有可能造成失傳的后果,以后難以彌補;同時也提示我們,由于個人條件不同、所處環境不同,有些前人創造的藝術高峰是不可超越的。你可以另辟蹊徑,自創特色,但談超越要慎重。京劇界誰敢說超越了梅蘭芳、周信芳、程硯秋?越劇界誰敢說超越了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徐玉蘭?三是活的人對活的人的傳承,在傳承者和被傳承者之間存在著交流,老師不僅把怎么演、唱教給學生,而且把為什么這樣演、唱和自己的體會傳授給學生,使其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學生有不懂、疑問也可直接向老師請教。老師發現學生有不夠的地方,則及時糾正,一遍一遍示范。過去強調口傳心授,這是符合戲曲傳承規律的。
二、形似與神似。
越劇傳承中經常遇到“像”與“不像”的爭論。想必大家都常常聽到這種說法:這位傳人和老師演唱得太像了,好!或者某位傳人不像老師,走樣了。以“像”與“不像”作為傳承得好與不好的標準,對不對呢?我覺得對此要進行分析。首先,作為傳承,我認為應當把“像”老師當成一種要求,就如同學習書法,首先必須描紅一樣。老師的表演、唱腔好在哪里,有什么特色、什么光彩,哪些地方有獨創性的特殊處理和獨到的技巧,首先要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學到手。這方面不能偷懶,不能走捷徑。不過,“像”也有兩種:“形似”和“神似”,學戲之初,往往先求形似,就是先學外部技巧、整體輪廓和框架,在直接訴諸聽覺和視覺感官方面給人以逼真地類似老師的感覺。但是,僅僅“形似”是不夠的,真正把老師的藝術精髓傳承下來,必須要求“神似”。“神似”,就是能夠學到老師塑造人物包括表演、唱腔的神韻,能夠從心底感知藝術形象的精神、氣質、性格特征,并活生生表現出來,使觀眾共鳴、感動,這是一種更高的藝術境界。像錢惠麗,最初學徐派、學演《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是先從曲調、動作的模仿學起的。這種模仿,是傳承必經的一個階段。但是她并沒有滿足于此,在《紅樓夢》演出千余場的實踐中,她深入理解了人物,也深入理解了徐派。王志萍初出茅廬時,人們驚喜地稱贊她模仿王文娟惟妙惟肖,甚至對她連扮相也酷像年輕時的王文娟贊不絕口。但王志萍沒有在贊揚聲中飄飄然,她在“形似”的基礎上力求把握王派神韻,成為優秀王派傳人。方亞芬演出《西廂記》、《祥林嫂》等袁派名劇,起初也是更多形似,但隨著藝術經驗的積累、生活閱歷的豐富和對人物、對老師理解的深入,現在再演出就有了明顯的進步,袁派的魅力通過她的傳承使越來越多的觀眾為之陶醉。當然,形似和神似之間沒有一條截然割裂的界限。神不可能離開形,否則無法被人感知;形若離開神,就徒具軀殼,無生命可言。
三、在傳承的基礎上創新,在傳承和創新中延綿劇種生命。
傳承的主要目的,是使非物質文化遺產不致流失、泯滅、消亡,因此首先要把前人創造的成果學下來,要強調繼承的重要性、必要性、長期性。傳承不是一時的臨時任務,而是劇種發展中永恒的要求,是生命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應該懂得,要學好、傳承好是不容易的,在戲曲藝術中,努力再現前輩的成果也是劇種發展的需要,是觀眾欣賞的需要。趙志剛在上世紀80年代初師承尹派后,演出尹派名劇《何文秀》連續七十多場,觀眾為什么如醉如癡欣賞他的唱?關鍵是尹派的魅力。尹派擁有廣大觀眾群,尹桂芳離開了舞臺,觀眾從她的傳人的演出獲得審美滿足。我們不能一概而論地否定模仿。某種意義上,沒有模仿就沒有流派。流派的形成和壯大,就是要“流”,包括流傳、流行,有一批學習、模仿得很出色的傳人和愛好者。但是,如果不是把劇種僅僅當成活化石,還應該重視在傳承的基礎上創新。因為時代不同、劇目不同、觀眾不同,每個演員的條件也不同,自然要有獨創性。袁雪芬是越劇界的老前輩,她就從不要求他的傳人僅僅學自己、像自己,而要廣學他人之長,創自家之新,因此曾師承袁派的戚雅仙、呂瑞英、金采風、張云霞都創出了獨樹一幟的流派。現在尹派傳人比較多,趙志剛、蕭雅、茅威濤、王君安都出自尹門,但已經呈現出不同風格。我們不要談到傳承時就與創新對立起來。事實上,在我們前面講到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里就講到:“各個群體和團體隨著其所處環境、與自然界的相互關系和歷史條件的變化不斷使這種代代相傳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得到創新,同時使他們自己具有一種認同感和歷史感,從而促進了文化多樣性和人類的創造力。”在傳承的基礎上創新,在創新中延綿劇種生命,越劇定會薪火相傳,保持旺盛生命力,適應新的時代。
聲明:本站所有文章資源內容,如無特殊說明或標注,均為采集網絡資源。如若本站內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權益,可聯系本站刪除。